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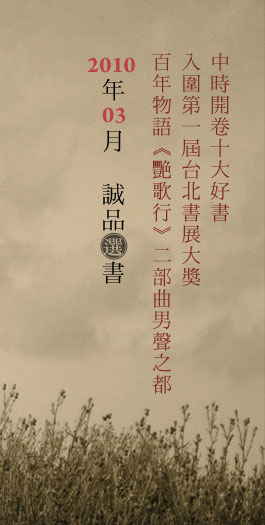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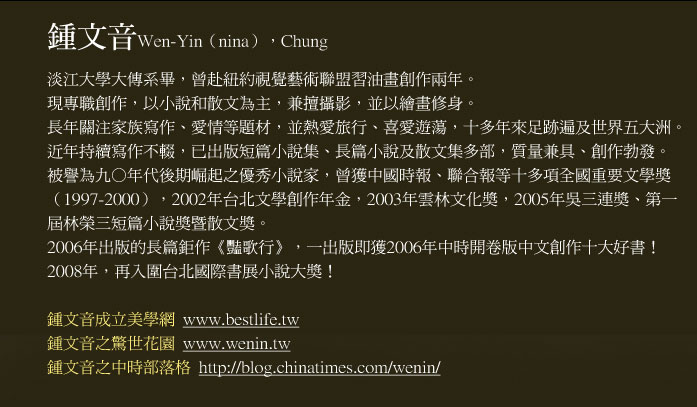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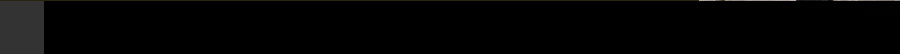

六十年前的春天,在紗帳背後的母親抱著他,他努力地想把母親手中的手帕推開,好讓自己的臉可以貼近母親的胸膛。佛手柑和沉木香的氣味,他幼年時最喜愛的味道從長年茹素的母親胸口飄出。母親被村人廣稱為呷菜阿嬤,不論比她小或者比她老的人都這麼地叫著她。他好多年沒見母親了,他不禁開口叫了聲「阿依」,但欲叫卻無法張口,才發現自己已經跨到另一個世界了。 他看見孩子鍾聲剛出生時臍帶繞頸,臍帶如念珠一圈圈地繞在孩子的頸上。母親仙麗看著這一幕邊幫新生孫兒剪去臍帶,邊嘆氣說,這孩子和佛有緣,但卻執意投生這五濁紅塵啊……他看見愛子逐漸牙牙學語,看見長大的愛子背對台灣海峽沉思的背影,看見愛子倒在海洋的身體,他伸手想要拉愛子,卻發現自己無能為力。 他看見從濁水溪上岸的洗衣婦人,他看見昭和四年他的孩子在一場大汛中死去,他看見自己步行在港仔墘,低頭看那無水無流的河津渡口時的悵然神色。他看見嘉慶九年祖上決定渡海來台的身影,他看見許多人,卻唯獨看不見自己。 他已經躺在烏心石棺木了,人的記憶可以維持多久?如果只有靈魂而沒有身體還能稱人乎?漁觀的靈四處飄著,甚至飄到了對岸。 這台灣上等好木的氣味環繞四周,環顧一切往事後,他才看見自己的最後肉身正被仔細地消毒著,這氣味像是他一生的總結。接著棺木四周塞進紙蓮花和黑木炭,然後他看見自己被子孫作最後的巡禮,子孫們在他的身體掛上菩薩金飾與彌勒翠玉佛。他的肉身只餘一層薄皮包著骨,原本就不高的他更是縮得好小好小,像是個老小孩。那一刻瞻仰其遺容的三歲曾孫伯夷竟噗嗤笑了出來,旋即他被快速抱開。 漁觀笑著,他想本來葬禮就該笑的,為什麼要哭,淚水比雨水還無用,何況我還在啊,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而已,還是這曾孫通透。 他很高興自己可以安然入土,回歸自己的土地,這片土地四周的田園都是他從祖先手上再加之擴大的。漁觀想:如果能嘗一回天皇獻納米的滋味就好了。漁觀望著眼前這一切,但卻看不見蛀蟲已然噬遍鍾家宅院的每個角落。他知道日後他的幽魂將會沾黏在神主牌,在他的三魂七魄裡,有一魂一魄就被收納在這張小小的木牌了。不過是張木牌,經道士喃喃唸誦一番急急如律令,末了以毛筆蘸了硃砂,他的其中一魂就附身在這個木牌了。(只是這有著魂魄的神主牌,眾人沒想到有一天會漂流在大水中。) 三擲筊,哭杯。鍾聲擲無。 做七期間,鍾聲常佇立田園,任從濁水溪虎虎上岸的冷風吹襲。他想父親家大業大,父親是成家子而不是敗家子,但父親竟就這麼地走了。 鍾公漁觀生於一八九三,歷清、明治、大正、昭和、民國,卒於民國一九四六年。他曾用十包稻米換得一座無用的山坡地,那片山坡地植著滿山坡的苦楝、油桐和相思。他曾以米賑災,修橋鋪路……他的子嗣繁多,他的戶口名簿裡還有牛戶,每一隻牛都入戶,都是他的財產。 鍾聲的腦子亂轉,想著亡父的訃聞該怎麼寫時,忽抬頭見到窗外父親早年植栽的一株相思樹在風中不斷抖動搖曳,他忽感泫泣。前幾天連父親養的老牛個個都提不起勁,有的甚且生病了,日日眼屎眼水圈在眼周裡,讓他見了跟著很傷心。 在這寂寥小村,莫名沉鬱的孤單總是自深處湧上。 他為了寫父親的訃聞,重新找了關於父親的許多信件和遺下的種種,他也在守靈時和父親從各地返回祖厝的兄弟們聊著昔日軌跡。村莊人也陸續來向漁觀持香頂禮,這裡的人並不怕死人,他們甚至很熟悉死亡儀軌。村裡的小崙橋興建好時,村人很高興終於有了橋梁可以橫渡田與田之間的大溝渠,但說來這溝水並不豐沛不湍急,但卻在橋搭好後,每日黃昏都傳來有人落水,且落水之後就快速被沖走,彷彿有一股強大的力量在拉扯牽引著落水人。村長覺得奇了,沒橋時,大夥繞著田走,也沒事。後來找搭橋的工人來問,才知道原來這鋪橋的木頭竟是拾骨後的棺木板,棺木有魂,每至黃昏暗暝,就來抓行走牆上的雙腳。把棺木板卸下移除,換上全新的樟木後,落入溝成水鬼的事就沒再發生了。一直到村莊有個廖姓閨女因被男友拋棄後上吊身亡,每至夜間她就手持七星劍到處晃蕩,嚇得能穿透黑暗神秘事物的嬰孩嚎哭不止,後來村人請作法事,讓金府千歲收伏這可憐深情女為夫人後,這鬼魂擾民之事也才又安靜了下來。 所以說亡魂和這村莊人也是老友了,亡魂就飄蕩在村莊角落,燐火照路,村人心頭仍篤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