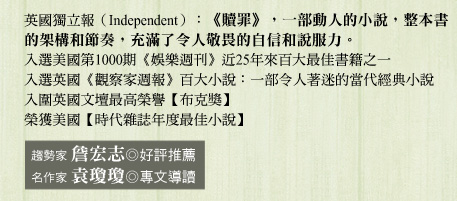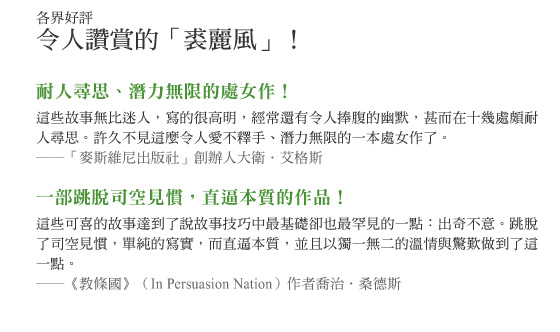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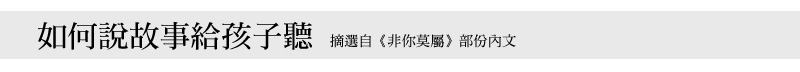
| 湯姆做了壞事。而此時,他似乎是自食惡果。能說的話也差不多都說了,所以我問起他太太。 莎拉願意談嗎? 當然,可是她很麻木。她壓根兒就不在乎。 真糟糕。 是啊。 那個學生呢? 她照樣肏他。 喔,要命,真要命。 是啊。 那她知道你、你的事──你有外遇? 不知道。 我們默然而坐,啜飲著茶。要命喔,十二年前我居然也在裡頭和稀泥。我用手指擠壓冷掉的茶包。幾分鐘後,我們擁抱,各走各的路。 他有幾個禮拜沒打電話來。這在我們的交情裡是司空見慣的事,剖白,再撤退,可是我忍不住納悶。我納悶我們上一次的談話是否就是拉開了序幕。嚴格來說,不是上次的談話,而是其間的沉默。飲茶時有許多的沉默深淵;回想起來,我能想像一手按住他的手,跪在其中一個黑暗深淵裡。而在這樣的深淵中,還有誰能確定自己的一舉一動嗎?你可能會向朋友尋求慰藉,而且真的照字面上的含意進入這個朋友,以便得到慰藉;而這個朋友,是很熟的老交情,可能會給你格外費心的照顧。心裡就是懷著這分情誼,我給湯姆寄了電子郵件。 午餐吧? 孩子的湯餅會,湯姆的母親拿著寫字夾,繞室一圈,指派所有賓客在某天某日要送健康餐給新父母。這叫做餐點樹,就像電話樹。我收到的指令是,要是湯姆和莎拉沒有應門,我應當把餐點留在門廊的提籃裡,而提籃外會貼著一張紙,寫著:謝謝你們,好朋友! 幸好,我被指派的是最後一天,我希望日子一天天過去,時間可以帶我遠離恐怖,奔向喜樂。可是那天來了,我卻一絲的喜樂也沒感覺到。我輕輕敲了他家門,希望能把餐點留在謝謝你們,好朋友的籃子裡,其實籃子上寫的是餐點放這裡。可是大門立刻就打開了。 小黛,謝謝天,妳來了,妳能不能抱她? 嬰兒就這麼塞給了我。湯姆領著我們走過涕淚縱橫的莎拉面前,她嘲諷地揮揮手,進了辦公室兼嬰兒房。湯姆盯著我,抱歉地眨眨眼,關上了門,留下我和嬰兒。先是一片靜默,緊接著。 我沒說那種話!我說只要我想做就可以做,因為身體是我自己的! 我屏住呼吸,把孩子抱在胸前,好似她是我的。一陣漫長的沉默,我想像莎拉是在無聲哭泣。可是突然間,她的聲音響了起來,清澈爽快,不帶絲毫的歉疚。 他們處於對我而言太過蠻荒的荒野,他們是跟野熊住在一起,他們就是野熊,他們的話從致命的野獸利牙間溜出。我真希望這些話是經過二手,甚至三手的傳播才傳到我耳朵裡的:「我們大吵了一架,」「我聽說他們大吵了一架,」「我認識的人認識一對夫妻,是本世紀早期的那一代,他們大吵了一架,不過說不定吵架對他們是家常便飯,我認識的這個人也不是很清楚,她現在才弄清楚她其實不算真的認識這對夫妻,因為她對人家的丈夫有非分之想,咳,她這個非分之想比起這場不知道多久以前的大吵又不知道要早多久了。」 湯姆開始尖叫,我不禁懷疑嬰兒柔軟的頭顱會不會在此時此刻因為暴力的刺激而變形。我盡量以理智來處理這個噪音,保護嬰兒的小小心靈。我低聲說:聽男人尖叫不是很好玩嗎?那不是違反了我們對於男人能做什麼的約定俗成的觀念嗎?接著我嘗試,噓──噓。 她把臉埋進我胸前找乳頭,我讓她含住我一根手指。她在我懷中睡著,我發現我腦中唯一有的想法是像宇宙論那麼宏觀的。我思索著太陽的球體,食物循環,以及時間本身,有似奇蹟,而且鮮活生動。我蜷起身體護住寶寶。湯姆和莎拉只是遙遠的交通,伴著我初始的開花期,我的心幾近痛苦的擴張,以便容納他們的沉淪。我研究每一根縮小比例的手指,我凝視她閉上的眼睛和莊嚴的睫毛,以及將來會很漂亮的鼻子。但我不記得她的名字。我注視她的臉。莉莉雅?不,沒那麼天真,應該是更聰慧的名字。我瞪著架上一個填充兔子玩偶及一排木頭雜耍小丑。拉娜?不。小丑又俯身又彎腰,最後終於對準了焦點。他們不只是雜耍小丑,還按照字母排列,而且會一輩子扭曲著肢體,就為了拼出「黎恩」這個名字來。 摘自大田八月新書《非你莫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