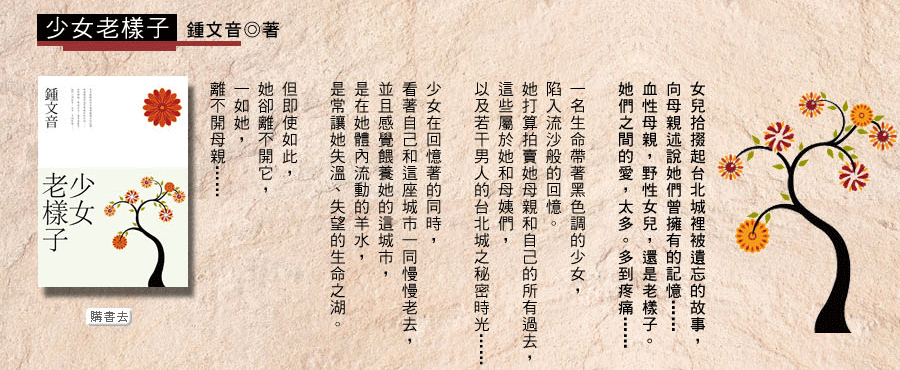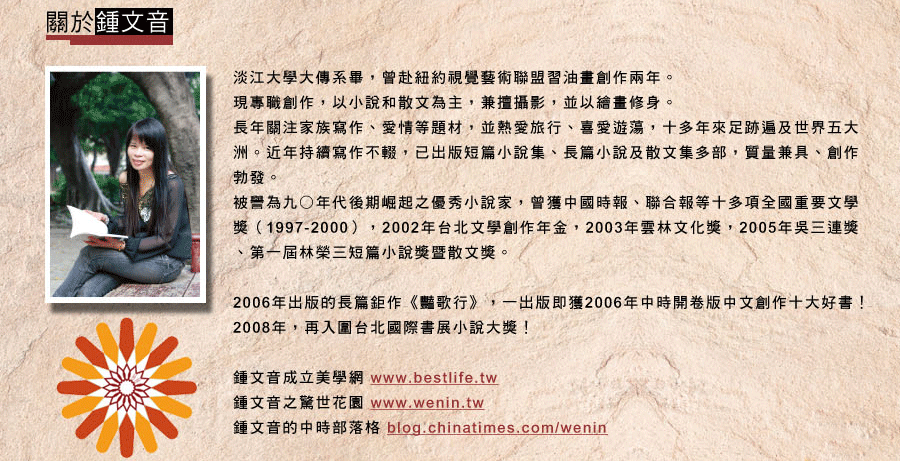| 王浩威開場說,他和我一樣喜歡旅行,嚮往心靈世界的東西。這也是他想和我對談的原因之一。 有人問我為什麼要把(豔歌行)寫得那麼長?把感官不斷地拉拔到「滿潮」之感? |
我說:我寫(豔歌行)的「豔」,表面是豔,底層卻是腐朽。 就像一朵花,開到極豔之後,緊接著是腐朽。可以從書裡滲透到這種氛圍.....什麼都發生了,也什麼都飛灰湮滅,我直視青春那些刺眼的(端不上台面)的東西。
王浩威說:自張愛玲以降到當代小說家,很少有女作家用這樣的「氣味」來處理情慾。 我不想寫知識譜系的東西,我知道抓卡爾維諾,抓波赫斯....滔滔論述或者繁衍知識很容易就讓人十分「敬畏」。但那些東西冷冰冰的,我想寫的是有溫度的東西,想寫的是敬畏生活的本身,即使我寫起來不偉大或者還可能有些小瑕疵。 我說其實我不是在寫男性式的「大河小說」,我只是在寫三個時空的「命運」與「際遇」。比如「豔歌行」鎖定後八0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的台北女子之感官愛情生活,極其豔麗與近乎腐朽的生活。「短歌行」則是寫戰後到七0的疾病與罪惡,想寫人之惡與一個家族的病與不幸。各種「短」暫的人生。「傷歌行」寫的是日據時代雲林的莊園鄉紳故事,鎖定台灣的「仕紳與商人」莊園的繁華與幻滅生活。 三段時空,凝視三種人生。我寫的不是「大河」小說,其實還不如說是「小溪」小說。各種小人物的哀歡。 我說我喜歡莒哈絲,是因為一種精神的嚮往,那種寫作到不要命的樣貌很動人。 至於自由的是心,現實其實也是殘酷的,是沒有什麼資源的。我其實不是一個有紀律的人,我其實很嚮往成為一個有紀律的人,早上寫作,晚上閱讀。但我常常很隨性,想寫就寫,沒靈感(釣不到魚時)就放著。我很想要每天去慢跑,但每次起床都已經很晚。久了就想,算了罷,反正二十幾年已是夜貓子,就順著自己的時間表吧。 也是會疲憊的,但每回疲憊就想起莒哈絲,那種義無反顧的東西。那種力量都是我匱乏的。 現實是於我困頓的,因為經濟常有問題。說來好像因為這樣,使我也一直寫了下去。 反面有時候也是一種動力。我想我生命裡還是有些能量,可以把負面的東西轉為一種光亮。持續把自己捲進寫作的齒輪裡,且還維持一種波西米亞的樣貌,我想應該是我想做的吧。 我說:母親買的啊,是我在付錢。且還貸款甚多。但母親的好意,也真的把我拉住了,使我有責任感。 也不至於到處租屋。過著居無定所的生活。但我還是用很低很低的生活方式維持了生活的美好品質,包括只用三萬元裝潢油漆動手自己的房子等等。人生的價值還有很多,絕對不會是「金錢」。我不會因為金錢而把自己交出去,甚至為了「名」,比如國中課本要收錄在(昨日重現)寫的一篇文章,但對我其中兩個自創的名詞有意見,要修改。我當然不願意,且還寫文章登載聯副批評教育的「格式化」「標準化」,不知道啟蒙心智才是最重要的事。我才不願意小孩子「背」我的文章,也不願意我的文章收在課本裡,可能旁邊是韓愈或柳宗元呢。我覺得孩子終究會長大,他們在書店裡發現我也許我會更高興。有作家看了聯副打電話給我說,妳幹嘛批評教育,改兩個字有什麼關係。說我真笨,妥協一下就好了,何必失去收錄在課本的機會。我說:這不是妥協的問題,這是人格的問題。 王浩威也說,年輕時那些有夢想的朋友,到了後來他們卻成了年輕時自己批評的那種人。 我說:沒錯,時間過去,許多人都改變了。 我笑說:可能舊疾復發。有些病要治療好幾年。其實我雖然說是「治療」,但其實治療是一種抽象的東西,寫作的精神永遠也療癒不盡的,因為心念相續...... 座談結束,我替這個美麗,有著眼睛深邃的小讀者簽名。
|